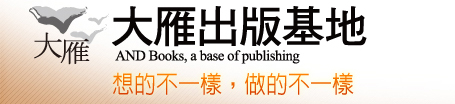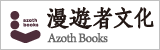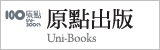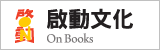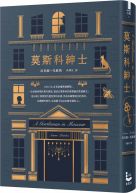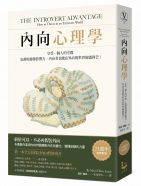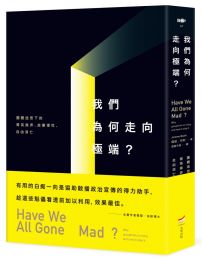本書談論一種大規模的集體道德思考:團體迷思(groupthink)。書中將探討新科技帶來的衝擊,不僅人際溝通,連我們的思考方式和自我認同、對彼此的寬容態度乃至政治,都深受影響。文中極力為理性、科學和歷史辯護,並敲響一記警鐘,呼籲大家挺身保護自由民主。早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和封城前,這個世界似乎就已日漸失去理智、陷入焦慮,人們的精神狀況不斷惡化。在這之前,世界普遍處於和平狀態,而且全球人口健康、福祉和經濟都已明顯改善,在此情況下走到如今這種窘境,可說是非比尋常。回顧我至今的人生,全球不平等的現象已大幅減少,農業技術足以因應全球的人口成長前景,以少於目前的土地供應充足的糧食。
面對一連串危機,我們的事前準備顯得左支右絀,而當危機真正降臨,我們又總是無法妥善處理。原因何在?我們的政治似乎有部分功能失調,與選民之間少了互動。政治菁英和媒體有時彷彿活在自己的泡泡中,與代表大多數人的輿論斷了聯繫。
難不成這世界瘋了?我們能否從現況中梳理出模式和原因,試圖阻止一切失控?
為何防疫政策沒有考慮到封城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為何二○○八年爆發金融危機,而且未來還有可能重蹈覆轍?近年來為何湧現政治正確的浪潮?淨零排放是明智的嗎?而我們負擔得起代價嗎?為何人們對民主的理想破滅?
我寫這本書是想試圖解釋目前發生的事。我認為,綜觀以上問題和近期的其他疑慮,我們始終未能看見令人滿意的回應,而從回應中至少可發現一個普遍情況。大規模團體迷思逐漸蔚為趨勢。我主張,目前社會上的混亂與不滿日益惡化(包括許多人對政治菁英和主流媒體提出的想法和詮釋感到疏離),若能借助我們對心理學的認知,輔以部分後現代的惡意迷因(這裡是指深植人心、像認知病毒般在社會中自我複製的那些觀點),最能釐清頭緒。此外,近年來通訊科技的變遷(尤其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已對人際溝通及互動造成深遠影響。舉凡我們的人脈和社群、身分認同、歸屬的群體、價值觀和道德體系,以及對他人的包容,無不受到影響。不僅我們源自石器時代的腦袋尚未適應這一切,我們的社會和政治系統也跟不上變化的腳步。
大腦演化比科技進步的速度更慢,早已不是新聞;大環境錯綜複雜,我們必須仰賴思考捷徑來理解龐雜的事務,也不是新鮮事。不只是行為規範,包括標準思考模式、概念聯想和是非觀念,都是思考捷徑。思考捷徑相當常見,無可避免,而且極其實用,但也可能使我們陷入困境。如果每個人的想法和價值觀不同,思考捷徑可能會遭遇有意義的挑戰;若所有人都抱持相同想法和價值觀,便可能形成「集體不理性」(collective irrationality)。面對環境中極為顯著的變遷時,假若我們固守共同想法和思考途徑,可能會感覺失望透頂。要是這些思考捷徑因任何原因而快速改變,我們也可能深感難以應對。然而,瞬息萬變的人際關係和互動,都是形塑思考捷徑的因素,在此前提下,如果這些變化不是隨機發生,而是有人為了利益或掌控權而刻意操控,狀況就會格外令人擔憂。
在集體不理性的多種形式中,團體迷思尤其危險。只要一套部分或完全錯誤的理念未能受到有效質疑,而持續存在於世,這種現象就會發生。團體迷思會不斷壯大,而深陷其中的當事人往往毫無察覺。最糟糕的是,團體迷思成了二元的道德競技場,善惡對立,非白即黑;要不全心全意相信,就是非我族類,沒有質疑的餘地。違抗者可能遭受欺凌、排擠、懲罰,深信不疑者則使出渾身解數,阻止任何挑戰或辯論。
不管有意或無意,迴避批評及拒絕多方思考是滋生嚴重錯誤的溫床,歷史上相關實例俯拾皆是。美國心理學家歐文.賈尼斯(Irving Janis)廣為宣傳團體迷思一詞,刻意和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雙重思考」(doublethink)相互呼應,並用以解釋甘迺迪(John F. Kennedy)內閣欠缺批判性的思考模式,終而釀成一九六一年美國意圖入侵古巴失敗一事,此即眾人皆知的豬玀灣事件(Bay of Pigs disaster)。研擬軍事策略時,他們並未充分留意計畫缺失,也未思考其他替代方案。討論只聚焦於沒有爭議的決定因素。內閣以為,總統支持入侵行動,沒人公開挑戰決策的整體思維,僅質疑其中的細節是否合理。後來,甘迺迪坦承計畫的確有所疏失,並採取因應措施以防日後復蹈前轍。一九六二年發生古巴飛彈危機,世界似乎就要爆發核戰,所幸前一年的教訓成功轉化為改進的養分。面對蘇聯在古巴部署核武,將軍事威脅推進到美國外海,甘迺迪召集團隊研討各種因應策略。他與團隊刻意保持距離,以免個人的初步觀點影響團隊判斷。
過程中,政策歷經激烈的辯論攻防,團隊也嚴肅思考各種選項。有別於豬玀灣事件的慘痛經驗,這次美國政府做出正確抉擇,獲得成功結果。
從那之後,賈尼斯提出的團體迷思概念備受管理顧問青睞,應用於指導企業董事會做出更完善的決策。他指出團體迷思的八個表徵:
(一)表面上看似無懈可擊;
(二)集體合理化;
(三)對群體道德深信不疑;
(四)認定異議者刻意與群體對立,且道德意志薄弱或心術不正;
(五)對群體中的意見不同者施壓,逼迫其合群或離開;
(六)自我審查;
(七)貌似全體一致認同;
(八)以固步自封的思維防範並壓制群體中的異議人士。
儘管賈尼斯關注的是小團體的決策過程,但團體迷思也適用於整個社會。一旦發生大規模的團體迷思,群體對於「逆風」的恐懼加深,尤其在菁英身上更為明顯,於是默許的氛圍愈來愈濃。每個人開始自我審查,公共對話陷入僵局。光是抱持「不可能這麼多人同時誤判」的想法,便足以維持虛假的表象。有個詞語的確專門形容這種現象:大謊言(Big Lie)。
本書架構
第一章將探討團體迷思背後的心理。我們喜歡說自己是理性的人,但人類本就不是理性的。理性是我們發展出來替自身行為說話的手段,在當時說服自己,也在事件落幕後,向他人辯護。而且,愈是聰明、學歷愈高、見識愈廣的人,在這件事上,愈有說服力。因此菁英彷彿活在大泡泡中,與外在現實脫節。很多時候,政治人物和媒體菁英分子集體盲目跟風的情況,比他們周遭的人更嚴重。
我們有著不同的群體和身分認同,也擁有不同的道德基礎。隨著同一套思維在群體中反覆執行,並且愈來愈少受到外界質疑,這套思考模式便益加穩固,且有助於明確界定群體的凝聚力何在,但這同時也讓群體無法容忍異己。堅守共同價值觀並關懷群體成員,都是團體迷思得以茁壯的助力。
我也會探討風險和不確定性,並批判社會傾向捨棄更全面的成本效益分析,廣泛採取預防動機(precautionary motive)的陋習。一旦群體基於預防動機而只關注一項問題,就可能輕率地漠視衍生的副作用和其他問題。
第二章將探究個人行為方式在人際互動中占據的重要地位,並說明我們如何建立人際關係,此兩者其實極具深意。這些行為模式不僅影響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形成和地方社群,也會左右我們對民主的參與。新技術和科技巨擘的商業策略同時扮演重要角色,對長久以來民主與專制之間的角力揭示了新的意涵。
在第三章中,我會探討新媒體和過去通訊科技的創新如何引發重大的社會變遷。許多世代以來,我們的心理沒有太多變化,但科技則日新月異。印刷機問世,人人都能取得《聖經》,導致後來的教會分裂和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奪走中歐地區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現代的新通訊科技創造了龐大機會,卻也帶來許多我們還不知道如何處理的危害。與更多不同的人事物接觸,促使我們產生新的身分認同、行為動機和價值觀。如今,新政治主張不只振聾發聵,更躍升為主導力量。
在解放與自由的新時代——我稱之為「大解放」(Great Enfranchisement)——新媒體掌握了即將到來的願景。不過與此同時,世界也將歷經部族意識(tribalism)和恐懼的催化過程,而後不僅難與異己相容,更充滿憤怒,最終活在仇恨和苦難之中。
價值觀是新的部族色彩,「區分異同」的思維漸強。某人覺得是美德的價值觀,在他人眼中可能是偏狹的表現。在全力強調應固守道德邊界的群體中,只要有人質疑內部奉行的價值觀,便可能受到惡毒攻擊,而攻擊時常從社群媒體開始。如今,毫無惡意的推特發文可能受到匿名人士刻意扭曲解讀,使當事人的事業毀於一旦。社會大眾害怕這類無妄之災以及不合理的攻訐,因此畏縮膽怯,自我審查。
在各種資訊大鳴大放的新世界,我們接收哪些閱聽內容並非偶然。這多半出於我們自己的選擇,只是企業廣泛蒐集個人行為相關資料並希望藉此獲利,無疑也扮演不容忽視的角色。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已然降臨,而且不懷好意。
在後面兩章中,我會提供金融界和學術圈的團體迷思實例。我最早發覺集體不理性的現象,是從金融和經濟領域開始。第四章會提到二○○八、二○○九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我將解釋當初的幾點誤解和未察覺的徵兆,並說明為何未來仍有可能再次發生。此外,我也會講述量化寬鬆背後的經濟原理,簡單評論新冠疫情期間的封城政策,並分析目前還算新奇的加密貨幣熱潮。該章指出,不理性和團體迷思可能發生的場域遠遠不僅止於董事會,也可能出現於大型議論場合和競爭空間,包括理念之爭。不得不這麼說,許多人對事情的看法的確可能出錯,而追根究柢,絕大部分是因為陷入團體迷思。
寬容、自由、歷史、理智和科學備受威脅。第五章將為科學辯護,探討現下反理性的趨勢。思想和言論自由岌岌可危,政治正確的浪潮興起。自我審查的現象日益普遍。後現代主義和其他哲學思想與主張單一客觀現實存在的概念背道而馳,卻已廣泛散播,而啟蒙時代奠定的研究方法以駁倒假設為論證基礎,在科學發展過程中不斷精進,如今卻一點一滴受到侵蝕。客觀現實存在的想法已然遭到淘汰,現在每個人都有自己相信的「事實」。世人不再從當事人的道德角度觀看歷史,導致歷史逐漸失去應有的意義和用處,反而成了支撐現行道德觀的政治宣傳,而非理解人類的管道。篤信自己那套事實的人大肆攻訐科學方法,有些人甚至不再將懷疑論視為帶動科學進步的火車頭。
在最後三章中,我會更聚焦探討政治和現今民主面臨的威脅。第六章將回顧歷史上對於自由、民主和治理的概念,文中會提到專制威權和革命的幾種風險和規律。接著,我會點出社群媒體時代的幾項政治特色,包含團體權利抬頭所帶來的影響,以及政治理論和實務間的平衡。外交政策應符合國家利益,以獲得人民支持,但很多時候並非如此。我們似乎倒退到馬基維利主義出現前的時代,任由理想形塑對外的國際政策,不顧現實情況。我們是否正在走向反烏托邦的未來?
無論在公共生活或媒體上,愈來愈多荒謬言論大行其道、無法無天。許多人覺得,媒體報導失之偏頗,且正有系統地誤導社會大眾,政府和主流傳媒不只販賣恐懼,還散播各種政治宣傳。第七章將探討媒體和政治圈已如何嚴重喪失客觀和公正立場,備受各種行動呼籲所腐蝕。菁英分子最終落入團體迷思的窘境,不僅散布政治宣傳,與大眾的溝通「弱智化」,同時在過程中也讓自己「愚蠢化」。
在這樣的完美風暴中,自由民主無疑正受到威脅。領導者尚且無法妥善應對。他們並未帶來希望,也未能展現應有的勇氣,挺身捍衛理性和正當政策。政治人物反倒像是透明人一般,一味委任技術官僚制定政策,並利用恐懼操控社會大眾。第八章將提點如何對抗團體迷思,緩解此問題對公共生活的影響。
本書的目的主要是協助讀者加速掌握狀況,明瞭如何最有效地運用新的通訊科技,避免延宕而錯失時機。最重要的,是要防止自由主義和理性遭受侵害,最終落入非民主政治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