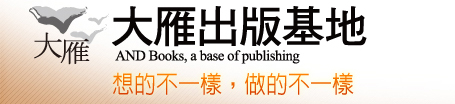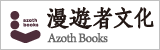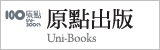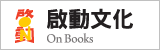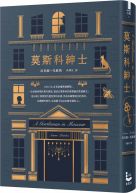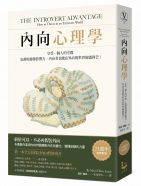何為精神疾病?
一六八四年,英國都鐸王政復辟時期才華洋溢的劇作家納森尼爾.李(Nathaniel Lee)被送進倫敦的貝瑟冷(Bethlem)一家瘋人院(日後Bedlam成了瘋人院的同義詞)。但納森尼爾厲聲抗議:「他們說我瘋了,我也說他們瘋了,可惡的是,他們人多勢眾。」
李在貝瑟冷瘋人院待了五年後號稱「康復」出院。出院三年後,他因飲酒過量致死,但他生前對於被冠上「瘋狂」之名的不滿,在三百年後的今天依然猶在耳際盤旋。誰才算「瘋了」?誰才算正常?誰說了算?
李這番不滿之所以至今適用,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人們內心始終對於罹患嚴重精神疾病感到畏懼。多數人內心深處總難免偶爾懷疑自己是否精神正常。每個人都會擔心,是否自己作為人最根本的明智判斷和自主性被精神疾病所把持。身為人,若失去這些,那還是個人嗎?納森尼爾眼睜睜看著自己行使理智的權利遭到傷害、自主權被剝奪,五年後從瘋人院出來後,整個人變得更為安靜,卻完全稱不上是已經治癒。沒多久他就與世長辭。他的人生遭遇駭人聽聞。我是否也會遭遇同樣的命運?
一般人之所以對精神疾病感到害怕的第二個原因是,界定精神疾病的分野始終不明確。像上文納森尼爾的例子,他的死活全掌握在一群所謂的「專家」手上。如今,精神病的診斷以及後續治療,取決於一群由複雜程序選出來的醫生、精神科醫師和精神衛生專家,偶爾還會加入法官的意見。由當代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所發表的診斷手冊,詳述精神疾病診斷標準程序,內容之鉅細靡遺可謂前所未見,但諷刺的是,這卻同時也是最取決於人而沒有固定標準的一套。
至少,在文件上看來,許多診斷決定,都取決於焦慮、憂鬱這種一般人也會有的感受之嚴重程度,結果就是心理健全和精神疾病之間沒有一個明顯的區隔。也就是說,不快樂和憂鬱之間的分界線究竟在哪裡?不快樂要達到多嚴重的程度才算是憂鬱?憂鬱要達到多輕的程度才算只是不快樂?而因為不放心而去檢查家裡門鎖和百葉窗要頻繁到什麼程度,才算得上是強迫症?而對他人的疑心要到什麼程度,才稱得上是偏執型精神病、妄想症和思覺失調症,顯示患者已經和現實嚴重脫節?
換言之,要如何確定誰患有精神疾病,而誰沒有?今天的我算在哪一邊?明天的我又會在哪一邊?
作為一名精神科醫師──專門治療精神疾病的醫生──這樣的問題和取捨我再熟悉不過了。而且這些疑問和爭議也的確不是無的放矢。精神醫學這個領域有太多東西沒有一個固定說法。樣樣都有爭議。
但情況也並非如一般人所擔心的那樣渙散或是隨便。精神疾病之苦是千真萬確,不容否認。看到有人明明飽受精神疾病之苦,且明明是可以醫治的,少有人能夠無視內心想幫助他們的衝動。這些都是千真萬確的。
面對這樣的侷限,精神醫學手法卻依然不改其高度取決於人的做法的原因,在了解精神病學的發展史後,基本上就可以理解了。我們正該從這樣廣的面向著眼,而非單就科學面才是。這樣才對得起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近數十年來,醫學界對人的大腦有更多的研究,但因為對於人類心智相關科學的知識不足,大大限制了精神醫學得益於神經科學進步。結果就是,儘管窮盡數代研究者的殫精竭慮,近來新發展的神經科學,幾乎無法為多數精神疾病患者經驗帶來任何重大的改變。雖然精神醫學界有些很有效的治療,但社會狀態和文化態度依舊影響巨大。沒錯,神經科學能見度和研究比重逐漸提升,但它並非全部,甚至到現在仍尚未成為主要的部分。
因為這樣,若想更深入且完整的了解精神疾病,就不能只是檢視一八〇〇年代至今的大腦相關研究,也要檢視社會發展的歷史:這一路走來,社會對於精神醫學的期待的轉變;以及這個備受爭議的學科過去充滿爭議的歷史;還有文化和地理在這裡面所扮演角色的演變;以及一系列左右著社會對於精神疾病態度的其他因素。本書要談的就是上述這些。
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本書算是旅遊札記。因為為了寫這本書,我踏遍愛爾蘭、英格蘭、比利時、義大利、德國、印度和美國。所到之處都讓我受益良多。
但本書同時也是一本歷史書,回顧了過去和當前,並透過古今來擘畫出將來。當然更重要的是,本書是精神疾病的專書,旨在透過不同個案病例,以及我身為醫師和精神學家的經驗,以求協助精神病患者。
全書最後,我改以宣言來結束。將我遍遊諸國的心得、想法和全書各章的探討,綜合出改善精神疾病患者與其家人經驗的具體方法。
這個做法對所有人都意義重大,而不只是對精神疾病患者或是有心理健康問題的人。我們會受苦、也會好起來,不管在家庭中、在群體裡和在社會上都互相扶持。
我們一定要做得更好。只要攜手合作,我們一定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