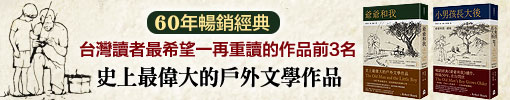符號學之「愛情=玫瑰?」
【一】
符號是啥?往複雜了說,可以複雜得不得了。我們的語言,就是人類使用最頻繁、最精微的,對整體人群來說都須臾不可或缺的符號系統。裡面又主要分為兩大層:聲音的和圖像的。
語言的聲音層,就是用嘴說和用耳朵聽的話。這連文盲也會。
語言的圖像層,則是手寫、印刷、鍵盤敲出的,記錄聲音語言的書面語言字元,靠視覺來辨認。
我們從小學開始的「受教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超越「文盲」階段的日常口頭表達,而逐步掌握更複雜的書面語言系統的「符號化」過程。這就是狹義的「識文斷字」。
對於廣義的「識文斷字」而言,一個人的話語符號運用與意義內化兩者,是雞生蛋、蛋生雞的一體兩面,識文斷字也就意味著概念、意義、思想,也內化於心,於是就能在語言藝術和書面閱讀中,以及自己的言說、寫作中,在「文化的符號之網」這一團亂麻中,交替地輸入和提取新的「意義」。
除了語言符號之外,音樂藝術,運用聲音的音高、強弱、節奏、音色來「符號化」,傳遞「意義」。美術呢,則運用輪廓、線條、色彩、明暗、筆觸、留白等來「符號化」,傳遞「意義」。而電影呢,自從默片時代結束後,就是把視覺呈現的意義和聽覺符號意義疊加到了一起,更不用說畫面還是在時間中流動的,聲音又分為場景音和畫外音。
這些事情,要多複雜有多複雜。於是就有了各種版本和各個門類的「符號學」。比如,要對符號的「層次結構」進行分類闡述,就有了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語言符號「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分層及其引申。若按符號的「類型和功能」來分,則有了皮爾斯(Charles Saunders Perice)的「icon」、「index」和「symbol」三分法。再比如說,對於語言之外的符號進行分析、研究、甄別,則有了音樂符號學、圖像學、電影符號學、文化符號學等—它們與音樂學、藝術史、文化人類學、傳播學等學科生成了錯綜複雜的交叉。
所以說,若往複雜裡去說,則這本書就不是僅僅一本書的容量,而要無限地擴容了。
還是就此打住,往簡單扼要裡說吧。
從何講起?先從「愛情和玫瑰」的關係講起,好不好?
這……貌似簡單—愛情不就是玫瑰嘛!
實則不然。
然與不然之間,隱藏著符號問題的神祕的真諦。
但你會問:這……跟「符號」,跟「意義」的問題,會有關係?
有的。
愛情是什麼?是人心裡面一種複雜的情感,是無法直接言說的。—若直接言說出來,則成為「我愛你!」、「我太愛你了!」「我愛死你了!」……總之,對於「愛」的各種表態,就算把「愛」字重複一萬次,也說不出愛本身為何物,怎樣愛,仍然是「愛」這種「人心裡面複雜的情感」的表述性「缺席」。「單純」的陳述性語言,無法表達、描摹複雜的東西如「愛」。「單純」的語言,能傳達「餓」、「渴」、「吃飯」、「喝水」、「睡覺」這樣的訊息,卻無法傳達「愛」的狀態為何物。
怎麼辦?詩人做到了。—把不可名狀的「愛」的「意義」,符號化為外在的玫瑰。十八世紀的蘇格蘭著名詩人,《友誼萬歲》(Auld Lang Syne) 的作者羅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在另一首迄今英語世界裡無人不曉,並佔據了當今無數明信片和網頁的詩裡說:「O, my Luve's like a red, red rose,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王佐良先生譯為「呵,我的愛人像朵紅紅的玫瑰,六月裡迎風初開。」
你看,「愛人」也好,「愛」也好,就和一種叫「玫瑰」的花草畫上了等號。—「愛情=玫瑰」。
我猜你會說:對嘛!詩人發現了真諦—愛情,不就是玫瑰嘛!
但我說「No」!
—玫瑰,一種薔薇科植物,與人類進入文明階段後的「愛」這種內在的隱祕情感,之間會有一毛錢的聯繫嗎?
玫瑰,不論是「羞答答的玫瑰靜悄悄地開」的玫瑰,還是「玫瑰玫瑰我愛你」的玫瑰,本身都不曾擁有你所賦予它的「意義」。其脈脈的情意、濃烈的情意,都是人類的「符號化」行為強加給它的。
如果玫瑰懂得人類語言,你跟它說,「你代表愛情呀!」它會感到莫名其妙,「別煩我!我對愛情絲毫沒有興趣,我和任何人類以外的生物一樣,只是以保存和傳播自己的基因為己任,與仙人掌、老玉米、蜜蜂或者蒼蠅沒有任何不同。」
如果玫瑰懂得人類語言,你跟它說:「你在中文叫玫瑰,在英文叫 rose,在印地語叫……」它也會感到莫名其妙。有莎士比亞的詩句為證:「我們用別的名字稱呼玫瑰,它也會芳香如故。」(《羅密歐與茱麗葉》)
但是,從詩人到廣告商,再到情書寫作者,都離不開「玫瑰」兩個字及其符號化意指,而且也離不開其他的一些符號化勾連,將星光呀、月夜呀、巧克力呀、「鑽石恒久遠,一顆永流傳」什麼的,強行與人類心靈內分泌的「愛情」畫上等號。
這麼說吧,離開了語言和其他符號體系的符號化運作,我們就無法把愛情這東西,「真切」地表述出來。沒有對玫瑰這樣的東西的指涉,就沒有愛情,或者說就無法讓別人感受到,當你想要表達出來的時候。而玫瑰對此一無所知。
你的內心世界的全部表達,往往就需要依靠對玫瑰這樣,與你一毛錢關係也沒有的東西的符號化。
語言,就是這樣運轉的。語言表達的高精尖集大成者是文學。各種語言和非語言符號體系運作的總和,是文化。
一首情詩、一部電影或一段 MV,絕不僅僅依靠「玫瑰」這一個符號而已,而是眾多符號相互之間形成複雜的關係,而且實現不同符號體系的交叉。對符號問題的解釋,就是對文學、文藝的魅力之所在的一種解釋吧。
按照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符號學原理》(Éléments de sémiologie)(文學院或中文系的同學你懂的)的描述,作為「結構層面」的「能指」(比如「玫瑰」),和作為「意義層面」的「所指」(比如「愛人」或「愛情」),構成「第一級符號」。「第一級符號」又作為「第二級符號」的能指,與新的「所指」共同構成「第二級符號」。這樣的「意指行為」(signification)還可以衍生出三級、四級乃至無限的符號系統,沒有終極。……比如說在 MV 中,先給出一朵嬌豔欲滴的玫瑰的特寫鏡頭,這個「能指」意象,指向了與愛情和愛欲有關的「所指」意義,構成了一個「第一級符號」。它也立刻成為新的「第二級符號」的能指,指向了新的所指—這時螢幕上緊跟著出現的一個女子嬌豔欲滴(請原諒我的措辭,舉例而已)的特寫鏡頭,成了第二級符號的所指,即這個女子就是前面的二級能指的愛情和愛欲的指涉對象。這是一個「蒙太奇」(Montage),一個表達「愛情」的「蒙太奇」。蒙太奇是電影發明出來之後,人類所調試出來的一種「視覺性修辭」。這個作為二級符號的蒙太奇,又會成為一個能指,指涉向新的所指,因為這個 MV 不會只有三十秒呀。一部兩個小時的故事片,其符號運作,想必比五分鐘的 MV 更加複雜了。
同理,從一首詩,一段 MV,到一個手機段子,一部長篇小說,在某種意義上—在符號學的意義上說—都是通過擺弄符號(「修辭」的、「敘事」的、「風格」的、「審美」的……),來操縱我們的視聽,潛入我們的心靈。
【二】
而實際情形,比前面舉例所進行的圖解要複雜得多。
前面我說了,「地球人」都會將「愛情」與外在的某個符號能指畫上等號。一位海外的著名人類學家曾親口對我說,在菲律賓南部某盛行「獵頭」習俗的土著部落,愛情=人頭,而不是玫瑰。因為,在那個部落要求愛,得先去殺人,提著人頭來送給心上人,作為愛情的標誌,就如同現代社會裡我們用玫瑰來求愛。想像若那個部落的「詩人」口占一闕愛情詩(他們尚處於不設文字的階段),或許是「我的愛,像鮮血淋淋的人頭」……
要點在於,不論是愛情=玫瑰,還是愛情=鑽石,甚至是愛情=人頭,都只有我們人類才幹得出來,因為我們就是前面說的「homo significans」物種—地球上唯一使用象徵符號的動物。遠古的人類,憑藉於此,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勞動過程中,以及協調勞作的溝通中,比其他動物要「高大上」許多。要不然我們的物種的學名,為什麼會叫作「智人」(「wise man」,拉丁文「Homo Sapiens」)呢。我們的智人祖先需要對事物加以標記、指認、分析,「與世界談談」,由此創造了符號,從此就能夠發現、描述和判斷事物和內心的「意義」,從而為赤裸的自然界和赤裸的自己穿上了符號的珍珠衫。這件珍珠衫其實是一副越來越精密的意義之網,從此就再也脫不去了。食欲,性欲,繁衍,排泄,死亡,群居,取暖,地盤爭鬥,這些原本遵從生物遺傳規律的活動,變成了烹飪文化,性文化,廁所文化,倫常,社會,建築,國家……
人類的一切物質和精神創造,總稱為文化(器物、工藝、技術、思想、生活方式)。對英國著名文化研究泰斗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來說,「文化是整個生活方式」。總之,凡是人類生活的創造,都是廣義的文化—是其他動物所不具有的。想想人為什麼埋葬屍體,開追悼會,過生日,舉辦婚禮、洗禮、「金婚」,為什麼要修建中山陵、醉翁亭、岳陽樓、毛主席紀念堂?想想中國人為何自古癡迷於玉石,要從遙遠的昆侖山採來和田玉,數千年而不絕?如此,草木山川、人頭玫瑰、金聲玉振,而皆有情,成為詩意的「能指」,從此「詩意地棲居」才有可能。人終日擺弄自己所創造出來的語言、文字、音樂等視覺聽覺符號。
文學、宗教、科學、藝術,都是符號系統裡的一些子系統罷了—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虛擬的巨大的符號世界。
無論是十八世紀的詩人羅伯特‧伯恩斯所在的蘇格蘭,還是尚不知書寫為何物的那個南菲律賓部落,因為都是人,都生活在文化「意義」中,和對文化意義的尋找、變更、再尋找中,所以都要為愛情的意義的賦予進行表達—通過符號化的畫等號來表達,不管符號等式的另外一邊是玫瑰,還是人頭。
那麼你可能又要問了:是「誰」在劃定能指(玫瑰、鑽石、人頭等)與所指意義(如愛情)之等號關聯的?為什麼會是玫瑰、人頭或鑽石?
回答這問題,連我都覺得「壓力山大」,知道這是直戳文學文化理論的永恆深處和學科前沿了。我只能邊回答邊總結。符號化的意義表達,是一件複雜的事,因為文化之網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包括文化、政治、經濟等各種因素。
所以,何不就具體看看人頭、玫瑰和鑽石這三個能指,是如何指向愛情的意義的。
先說「人頭」。
在泛太平洋諸多剽悍的島嶼部落中,殺人而獵取人頭,乃是最悠久的文化傳統,或者可以叫作「獵頭文化」吧。每一個部落,都處於其他部落的威脅之下,一般是捉到其他部落的人,大家分食之,然後將人頭進行風乾或藥物處理,收藏起來,作為藝術收藏品來把玩、炫耀。獵取外族頭顱,就起到安定團結本族的精神作用。而擁有足夠多的人頭收藏品的男士,則如今天的「鑽石王老五」一樣,能得到所追求的女性及其家人的青睞。這意味著地位和安全感。能夠獵殺越多別人的頭,意味著自己家越安全,離那種被獵頭的倒楣命運越遠嘛。
再說「玫瑰」。
這顯然來自西方文化,玫瑰是西方最複雜的符號象徵系統之一。想一想,中國古代詩歌,李白杜甫李商隱,以及宋詞裡面的愛情,有一首是詠玫瑰的嗎?玫瑰能進入中國人乃至亞洲人的文化想像和文化符號體系,靠的是一百多年來「西學東漸」的結果。玫瑰和百合,是《聖經》中喻表耶穌的花卉,象徵神的聖潔、美好,如「沙侖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讀過法國小說,大仲馬(Alexandre Dumas)的《三劍客》(Les Trois Mousquetaires)的讀者都知道,法國王室的圖案裡面有百合花造型,這肯定也是因為其自詡為奉天承運的基督王國。在中世紀的騎士文學中,愛的對象不僅僅是耶穌基督了,而可以是寓意上和字面意義上的女性。於是,那份強烈的愛的所指意義,就轉移到了男女之間的愛情和愛欲上面了,以至於在今天的東方乃至在西方自身,很多人已經完全不需要瞭解其來自基督教背景的意指轉移,就可以在通俗文化中看懂有關玫瑰的一切了。而在基督教文化之前,在古希臘羅馬文化中,當然也有玫瑰這種原產於地中海沿岸的植物的影子,但古希臘羅馬人文化,作為大半截兒都處於基督教興起之前的「異教徒」文化,對愛情、愛欲進行符號化的重鎮,是蘋果。
《荷馬史詩》中著名的特洛伊戰爭是怎麼打起來的?就是蘋果惹的禍。希臘英雄佩琉斯(Peleus)和愛琴海海神千金忒提斯(Thetis)成婚,奧林匹斯諸神都被邀請了,唯獨漏了爭執女神厄里斯(Eris)。厄里斯在席上拋下一個金蘋果,說它屬於「最美的人」。天后赫拉(Hers)、智慧之神雅典娜(Athena)、愛與美之神阿芙蘿黛蒂(Aphrodite)相爭不下,最後請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裁決。赫拉許以權力,雅典娜許以智慧,而阿芙蘿黛蒂則以美色為誘惑。最終帕里斯選擇了美色,抱得絕世美女海倫入春闈,而那場曠日持久、波瀾壯闊的戰爭則是後話了。這個蘋果,在基督教文明的符號體系中,也在《聖經》中擔當了重要的反派角色—它成了「誘惑」的能指,被夏娃和亞當吃進嘴裡,導致人類的祖先被逐出伊甸園。人類不斷繁衍、發展的歷史就此開始。蘋果由此成為性欲的象徵,而人類的祖先及其後代,為了這紅通通的欲望,不得不世代為它背負責任,忍受懲罰。這,就是原罪。顯然,玫瑰和蘋果本來都是「無辜」的,但在基督教的符號體系裡面,前者指向了從神傳遞到凡人的愛,及其昇華、擴展,後者則指向了來自人自身的欲和罪。玫瑰和蘋果的兩種命運,真是「天人永隔」呀。當代義大利的著名符號學大師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也來湊熱鬧,居然寫了一本以中世紀修道院為場景的暢銷書小說,集驚悚、懸疑、偵探、煽情為一體,題目就叫《玫瑰的名字》(Il Nome Della Rosa)!而最近在中外迅速竄紅的那首「你是我的小呀小蘋果」,則更是一朵匪夷所思的符號意指「奇葩」了!
最後說鑽石。
相比玫瑰、百合,關於鑽石的上古典故、文學軼事,實在是少得可憐。這種碳元素晶體,是如何成為價格高昂的美滿婚姻必備佳品的?秦漢宋元詩文中,愛情千古佳話中,古希臘、羅馬故事中,中世紀騎士傳奇羅曼史中,有哪一個是以鑽石當愛情信物的?至少對我這個沒有著意考證的一般人來說,所知甚少。只能說,它是英國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通過波耳戰爭(Boer War)趕走了荷蘭人,佔領南非,為了經濟增長點,為了佔領龐大的世界市場,發明出來「鑽石恒久遠」這種說法,讓有一點兒錢又躍躍欲試,需要掏錢來表達「something」的中產階級,掏錢來證明自己「真心」的一種昂貴道具吧?最硬的物質啊,不變心啊。—化學知識的演進,也是必要的。
一個關於愛情之符號能指的小小話題,就可以這樣複雜。這是因為人是使用符號,借符號來表述意義,棲居於意義之中的動物。人有多複雜,符號就有多複雜。反過來說也對:符號有多複雜,人就有多複雜。在符號的運作中,最主要的是靠語言符號的運作。在這個意義上,二十世紀著名的「闡釋學」大師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說,「能夠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真理與方法》(Truth and Method),洪漢鼎譯)